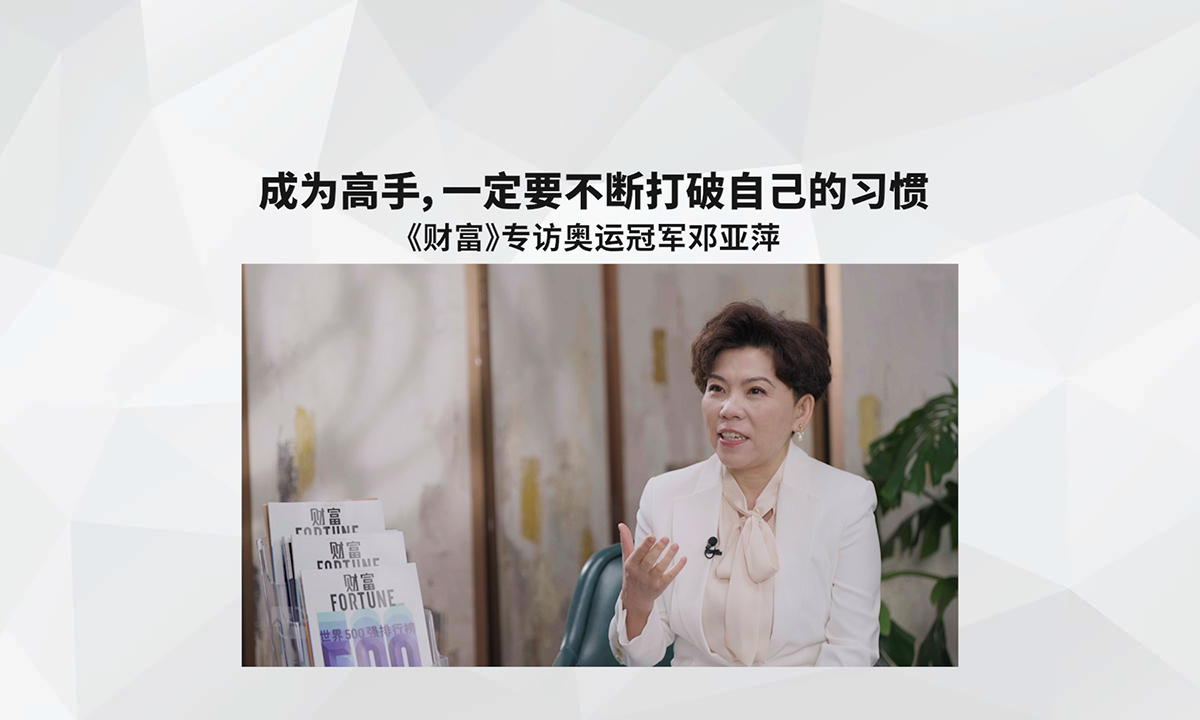CEO为何渴望碳减排法案
福特汽车、杜克能源和益可环境国际金融集团的高管都希望建立市场机制,刺激绿色技术投资。
作者:David Whitford
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Bill Ford)、杜克能源公司(Duke Energy)首席执行官吉姆•罗杰斯(Jim Rogers)和碳交易商益可环境国际金融集团(EcoSecurities)首席执行官布鲁斯•阿什(Bruce Usher)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都讨厌不可预测性。
这就是为什么罗杰斯多年来一直呼吁国会对限制碳排放进行立法,这样他就可以大力投资可再生能源。这就是为什么福特说他希望政府征收汽油税,这样他就可以对小型汽车进行投资。这也是为什么阿什希望国会能通过一项总量管制和交易(cap and trade)的法案,从而搞活美国的碳交易市场,刺激绿色科技领域的投资——趁现在还不算太晚。
本周二,阿什参加了《财富》头脑风暴绿色会议。他在有关碳融资的讨论会上说:“市场机制不但能够发挥作用,而且速度之快超过人们的想象。”
阿什的公司根据《京都议定书》规定的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开展国际业务。这一机制使得污染者必须为燃烧化石燃料付出代价,同时对绿色技术的投资给予奖励。从很多方面来看,当前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从事这一行尤为有利。但问题在于:京都议定书三年之后就将失效,而碳融资项目通常需要两年半的时间来开展。结果就导致阿什手头的交易流已几近停滞。
阿什说,现在要做的是建立起美国的总量管制与交易体系,就像《马基和维克斯曼法案》(Markey-Waxman)中提出的那样。阿什表示最理想的情况是在年底实现这一目标,但事实上他本人和贝克•博茨(Baker Potts)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事处气候变化事务的负责人比尔•邦珀斯(Bill Bumpers)都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时不我待。今年十二月,世界各国的代表将齐聚哥本哈根,讨论制定后京都时代的气候协议。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总量管制和交易问题上持什么立场?必须对其它国家有个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