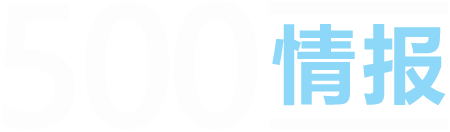预防为何无法“治愈”医保
美国政府称预防是负担全民医保的关键之一,实际并非如此。
作者:Matt Miller
政治分析中一条有用的原则是当所有人都同意时开始怀疑。因此,当两党在今夏的医保辩论中均对“预防”大唱赞歌时,我不禁开始挠头。这是唯一一项亨利•瓦克斯曼(Henry Waxman)和约翰•博赫纳(John Boehner)能达成共识的改革。别误会我的意思:官员们说得没错,我们的体系确实疯狂的倾向于等人们得了重病之后付钱给医生和医院对他们进行医治。然而他们就此得出美国早该有预防议程,并且此议程将解决飙升的国民医疗费用问题(甚至帮助为扩大的保险范围买单)这个想法,未免有些牵强。
斯坦福大学(Stanford)健康经济学家维克托•福克斯(Victor Fuchs)很久以前就指出了主要原因。大部分人一生中多数健康开销发生在去世前的5年中,此时身体部件经常一个接一个的开始崩溃。于是我们开出英勇的药物,同时运用不断创新的技术来延迟死亡的到来。无论怎样预防,都无法改变生命终结时的这种动态。
普林斯顿(Princeton)健康经济学家乌维•莱恩哈特(Uwe Reinhardt)表示:“预防能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我从未见到有分析表明,长期而言采用大量预防措施的社会的医保成本较低。”
延迟但不能消除某些花费的预防涅磐意味着,任何节省都将类似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看到的健康维护组织(HMO)的一次性出局。将花费压低是件好事,这一点毫无疑问。但说得难听点,在此处成功意味着将花费降低、较早的心脏病致死换成花费较高的将来某个时候因癌症或慢性病致死。对我们心爱的人而言,这好极了,但这无法阻止健康花费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0%。
有些形式的预防保健护理——例如儿童时期的免疫——成本较低而十分有效。但很多成本高昂。专家称,问题在于无论使用何种干预,一旦过度(因为难以瞄准真正的获益者)就会花些冤枉钱。举例而言,每年一度的体检和健康维护计划是好事——但这也需要对医疗保健专业人士以及显像进行先期投资,通常是为了那些原本未曾获得此类资源的患者。
斯坦福大学健康政策中心(Center for Health Policy)负责人艾伦•盖伯(Alan Garber)表示:“为数不多的将预防保健护理与治疗相对比的研究已经表明,这两种形式的护理都可能具备——或不具备——成本效益,这取决于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预防这一概念并无魔力,它只不过听起来不错。”
同样的,对于慢性病,预防只不过会延迟花费的产生。糖尿病患者接受眼部检查并让足科医生检查脚,以延迟像失明这样可怕的并发症或是接受截肢手术之需要。心脏病患者可能服用斯达汀、阿司匹林和血压药。上述措施能提升生活品质,但无法消除疾病,而只是延迟其发展。福克斯的铁律依然成立:我们最后都将患上费钱的病。
长期而言,可能改变局势的不是预防本身,而是行为的变化。预防——服用药物、接受特别体检等——可能对我们有利,但它也带来可能超过任何节省的社会成本,而且通常牵涉已有严重疾病需要应对的人。
健康的行为是圣杯:假如打从很小就养成健康的行为习惯,有可能从根本上降低我们染上多种费钱的慢性病之几率。而行为改变是可能的。
这正是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经常强调的,哈克比减了一百多磅的体重,这使得他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成为这个方面的权威。哈克比告诉听众“假如我们是在40年前开这个会,你们当中有一半人会抽烟,而另一半人不会介意。”他会说现在没人抽烟这一事实证明我们能改变自己思考和行动的方式。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林恩•尼可斯(Len Nichols)表示,改变孩子们对蔬菜水果以及薯片和块状糖的看法,最终能降低成本。尼可斯表示,假如我们久而久之减少肥胖以及新型慢性病的发病率——从而减少人们在走到生命尽头时出现极费钱的多种慢性病之可能——“影响可能极为深远”。
但即便我们幸运的话,那也任重而道远。目前,认真对待健康花费的唯一方式是重新设计提供护理的方式,而研究者认为此体系效率极低。但正如政客们所知道的那样,让医生、护士、医院、健康计划、药物和设备制造商改变其行事方式是件不讨好的差事——特别是当医疗保健“浪费”的每一美元都进了某个人口袋。
因此预防是此轮辩论中虚假的万灵药。斯坦福的盖伯表示:“政客们忍不住宣称我们能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使人们更健康。但假如事情真是这么简单,那早有人这么办了。”
马特•米勒(Matt Miller)是美国发展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名资深研究员,也是《别让过时理论统治我们》(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一书的作者。
译者:熊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