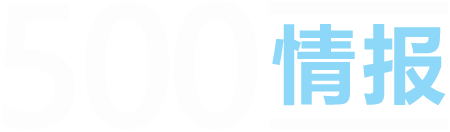彼得·德鲁克逝世十周年 | 彼得·德鲁克为我们指引的路
一直以来,人们可以依靠彼得·德鲁克为自己提供一种观察事物的新方法。毕竟,他是第一位认识到管理是一门值得深入和规范研究的学科的人。远在他人之前(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他就预测到了计算机技术总有一天将如何彻底改变商业。1961 年,他前瞻性地呼吁人们关注日本即将崛起成为工业大国,而在二十年后,他又警告日本将面临经济停滞。至于“私有化”、“知识工人”和“目标管理”等概念的提出,我们也可以都归功于他。
即使是在迟暮之年,德鲁克仍然充满了众人缺乏的洞见,并且对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渝。他兴趣甚广,从经济学、心理学、哲学、歌剧到日本艺术,无不涉猎,也曾经为成百上千家大公司、政府部门、小企业、教会组织、大学、医院、艺术机构和慈善组织提供咨询。甚至直到德鲁克逝世前一年,这位管理学大师仍继续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克莱蒙特研究生院(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管理学院开讲座,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不断前来加利福尼亚朝拜,向他讨教。
在2004年距离这位教授的生日还有两天的时候,《财富》自由编辑布伦特·施伦德(Brent Schlender)曾受邀,到德鲁克位于克莱蒙特的家里访谈。于是,有了以下这段德鲁克晚年少有的采访:
《财富》:信息技术对商业的最重要影响是什么?
德鲁克:信息技术迫使你更有逻辑性地组织流程。电脑只能处理答案为“是或否”的事情。它处理不了“可能”的事情。因此,重要的不是计算机化,而是你的流程要遵守的律令。在你将流程计算机化之前,你必须思考,否则计算机就会罢工。
这种强制的律令会带来一些不利之处,因为它通常迫使人们处理事情时过分地简化。此外,形成商业决策的过程并不总是很有系统性的,因而并不总是可以通过计算机来完成。你必须从决策者的想法中抽出各种假设,明白无误地将它们与检查这些想法的方法一起输入到程序中,只有这样计算机才能帮你管理决策。老一代的经理人发现,要搞得这样明白无误令他们苦恼,因为他们就是不想这样。此外,我们都知道,很多决策就像尿憋不住一样,是老板被迫做出的。
《财富》:既然企业如何计划和运营方面发生了这些系统性变化,你是否认为首席执行官的地位和作用也在改变?
德鲁克:在每次经济繁荣的时候,都出现对首席执行官的英雄崇拜倾向。聪明的首席执行官有条不紊地组建自己的管理团队。但那些人们经常提到的明星首席执行官当中,有很多不知道团队为何物。而且,首席执行官薪酬的膨胀,已经给管理团队这种概念带来很实在的破坏。我在克莱蒙特研究生院讲授的高管课程中,学生大都是很大的公司的主要部门的总经理,他们的报酬很高。但公平地说,对于他们那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当中很多人的报酬过高,他们是鄙视的。J.P. 摩根有一次说过,公司最高管理者应只拿普通工人 20 倍的薪水。今天则更有可能是 400 倍。我说的不是车间里的人们的辛酸感觉。他们已经确信老板就是窃贼。我说的是中层管理人员,他们的希望令人难以置信地破灭了。因此,目前的首席执行官危机是一场严重的灾难。让我再次引用一句 J.P. 摩根的话,他说过:“首席执行官只不过是雇来的人手”。如今的首席执行官忘了的正是这一点。
《财富》:对知识工人的生产率,我们能怎样衡量和提高呢?
德鲁克:还没有人真正考察过从事科研的白领工作的生产率。但每当我们考察的时候,奇怪的是都毫无结果。你知道,我最近以来的研究工作涉及的是大学、医院和教会,它们是最大的知识工人雇主当中的三种,其生产率是令人沮丧的。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根据定义,知识工作是高度专业化的,这意味著知识工人的利用程度通常是很低的。
知识工人缺乏效率,某种程度上是以下这种 19 世纪的信念的遗留结果:现代的公司试图自己做公司的所有事情。现在,谢天谢地,我们发现了外包。但我要说的是,我们确实还不知道怎样做好外包。大多数人是用削减成本的观点看待外包的,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外包所起的作用,是大大提高那些为你工作的人员的质量。我认为,对于那些没有可能进入管理高层的人的工作,你都应当把它们外包出去。当你把工作外包给一名全面质量控制专家,他就是在一年 48 个星期为你和其他客户而忙,他把这些工作视为挑战。而如果公司雇佣了一名全面质量控制人员,那么他一年只忙六个星期,其余时间则在写备忘录和找事做。所以当你外包时,你的成本实际上反而是在增加,但你得到了更好的效果。
《财富》:很多高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感到担忧,尤其是对学技术的人越来越少这种现实感到不安。你担心吗?
德鲁克:这种情况完全属实。但他们忘了两点。我们是唯一一个拥有重要的再教育体系的国家,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而且我们是唯一一个年青人可以很容易从一个领域跳到另一个领域工作的国家。这在日本是不可能的。如果你是会计,你就得是会计。这在欧洲同样是不可能的。但在这里,这样做很容易。
因此,与欧洲不同,在美国,我们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在于雇员的自我组织性。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当我的欧洲朋友移居到这个国家时,对于要面对的这种期待不知所措。让我们看一看这里很多人的职业生涯。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伊梅尔特曾做过五六种不同类型的工作──销售,设计,为不同的产品部门工作。相比之下,西门子的首席执行官任此职位前从未在德国之外担任过任何职务。
《财富》:你说美国经济如今受到了很深的错误认识的伤害。你能举些例子来说明吗?
德鲁克: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大家所想的有很大的不同。好像没有人意识到我们引入的工作岗位是输出的两到三倍。我指的是到美国来的外国公司创造的岗位。最明显的是外国汽车公司,单是西门子公司在美国就有 6 万名雇员。我们在输出低技能、低报酬的工作岗位,但同时也在引入高技能、高报酬的岗位。
《财富》:美国劳动力成本更高、制造业进一步移往国外会危害到我们的贸易平衡。难道这种说法不对吗?
德鲁克:工资成本如今只对很少几个产业而言是最重要的因素,即少数几个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总成本 20% 以上的产业,例如纺织业。我不知道正常的美国产品的成本中有多大比重可以归为劳动力成本,但这种比重很小,而且还在缩小。以汽车零部件为例。由于我提供咨询,我恰巧了解世界最大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当中的一家的内部成本结构。他们告诉我,与进口相比,在这个国家进行生产还是非常便宜的(或者说在沿美墨边境一带的边境工厂中生产时可能是这样),因为尽管这些零件是劳动密集性的,但设计和制造也具有很强的技术密集性。当属于这种情况时,我们在这个国家进行生产仍然可以干得不错。所以说,那种认为劳动力成本是在美国之外进行生产的主要原因的观念,只 是对很小一部分产业来说才能证明是合理的。
因此,正在将工作岗位迁移出美国的那些产业属于比较落后的产业。对于很多比较先进的产业而言,美国仍然是世界上从事生产的最便宜的地方。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们的工资和薪水很低,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给雇员的福利比欧洲低很多,而且美国工人更具灵活性。我在此说的不是你可以把会计人员调去从事工程工作,我说的是你可以把人从芝加哥调到洛杉矶去。在德国,你敢这样做?他们不会的。这是他们庞大而又有限制性的雇员福利制度的荒谬副作用之一:让一个人在鲁尔地区失业,比调他到斯图加特做一份实 实在在的工作还要便宜。日本也存在同样的情况。
因此,我所说的“不可见”成本正开始迅速变得比直接劳动力成本更重要。它们是:养老金成本,福利和医疗成本,尤其是某些还没有人评估的成本,我把它称为“报告”成本,它们基本上都是与遵守国家法规、税收、劳资关系方面的要求等有关的。
《财富》:你怎么看关于“美国存在失业问题”这样一种普遍印象?
德鲁克:似乎没有人意识到美国劳动大军占人口的比例最高,比例远远高于任何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西方,我们的长期失业率最低。我们确实存在的失业现象, 大多数并不是长期的那种,而是短期的,人们处在“找下一份工作的阶段”,这个阶段至多不过几个月。对于受过高等教育并想进入劳动队伍的人来说,我们提供的好工作最多。不像大多数欧洲国家,我们的大学生基本上没有失业。他们可能暂时没有得到想要的工作,而且他们可能第一年得不到年薪 7 万美元的工作,但他们得到了就业。最后,我们还要考虑到,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我们把所有想工作的妇女都吸纳进了劳动队伍,而且没有发生任何动荡。这是相当了不起的。
《财富》:让我们谈一谈美国经济的生产率问题。衡量生产率的数字不断地提高,甚至在增长迟滞的时期也是如此。
德鲁克:我认为你不能相信我们看到的有关生产率提高的数字。但毫无疑问,在制造业,我们看到在理论和体系方面发生了一些可以与 20 世纪 20 年代的产业革命相媲美的根本性变化。这些变化的发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将生产计算机化和自动化带来的,而是通过生产的系统化。在过去,人们提高生产率的方法是专业化。今天,我们设计制造流程并在某种程度上设计分配流程,与其说是使它们最大化,不如说是使它们最优化。而且,新的制造系统将弹性植入到系统之中,而按照我们目前衡量生产率的方法,弹性可能实际上会导致直接生产率的某种损失。
你瞧,那些数字衡量的是工作进行的时候的生产率,但它们没有衡量工作不能进行的时候的生产率损失,如你为制造某种不同的东西而建立工厂时的损失。我怀疑,生产率的提高实际上要比所有这些数字显示的更大,因为新的、更具弹性的制造流程切实地消除了设立工厂等设施的时间,而在此时,制造工作是不得不停止的。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设立时间从三个小时减少为四分钟。这并不会在我们的生产率统计数字中显示出来。这些数字也没有涉及能够改变生产的构成所带来的价值,因为它们专注于传统大批量生产行业的净产出。在我们一些较新的行业中,我们还不太明白如何衡量生产率。
《财富》:美国是否仍在为世界经济定调子?
德鲁克:美国的主宰地位已经结束。现在正在兴起的是由集团组成的世界经济,这些集团以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和东盟等为代表。在这种世界经济中,没有中心。印度正在很快变成一个强国。现在,新德里的医学院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班加罗尔理工学院的工科毕业生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毕业生一样优秀。另外,印度有 1.5 亿人以英语为主要语言。所以说,印度确实在变成一个知识中心。
相比之下,中国的最大弱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小得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在超过 13 亿的总人口中只有 150 万大学生。如果他们要达到美国的比例,他们就要有 1,200 万以上的大学生。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训练有素,但人数太少了。还有就是中国巨大的内陆地区农村人口过多、不发达。确实,这意味著制造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但在中国,吸纳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而又不引起动荡,这样的可能性看来很值得怀疑。你在印度就看不到 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在吸收农村地区多余人口进入城市方面做的工作令人吃惊──在没有发生任何动荡的情况下,农村人口从 90% 下降到了 54%。
大家都说中国的增长率达到 8%,而印度只有 3%,但这完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实际上并不了解情况。我认为与中国的进步相比,印度的进步令人印象深刻得多。
《财富》:回顾你的生涯,有什么事是你曾希望做但却未能做到的?
德鲁克:有,这样的事不少。我本来可以写很多比我写过的更好的书。我最好的书本来应该是一本名叫《管理无知》的书,很遗憾我没有写。
我不后悔拒绝亨利·卢斯的邀请,他当时请我出任《时代》杂志的国际新闻主编,后来又请我担任《财富》的执行主编。我想坚持教书,我想写我自己的东西,而当你为一份出版物工作时,你是无法这样做的。
我曾设想过做另一份工作,但也没有变成事实,对此我也感到很高兴。在结束了贝宁顿学院(Bennington College)的任教之后,我计划到哥伦比亚大学与一位朋友一起工作,他正创办一个美国研究系。当时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否决了资助的计划。他是削减开支的老手。我的录用已经得到学校基金受托管理人的批准,并已经拟了合同,当时就等著艾森豪威尔签字了。
就在被告知我没有得到这份工作的那一天,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在第 116 大街进了地铁站,这时候遇到了另一位老朋友,他在纽约大学教书。他跟我说他正要去哥伦比亚大学,找一些老师帮助他组织纽约大学管理学研究生院的教学人员。我甚至还没上地铁,就在合同上签了字。这就是我当时怎样当上管理学教授的。所以回想起来,对于哥伦比亚大学的那份工作当时黄了,我现在极其高兴。
译者:水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