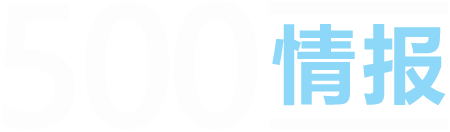梅琳达•盖茨亮相
她向《财富》讲述与盖茨如何生活、与巴菲特如何共事以及如何散财
作者:Patricia Sellers
早在和比尔•盖茨相识和结婚之前,梅琳达•弗兰奇(Melinda French)还谈过一场恋爱,对象是一台苹果(Apple)电脑。梅琳达出生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一个勤勉的中产阶级家庭。为了把四个孩子供上大学,她的父亲雷•弗兰奇(Ray French)一直节约开支,精打细算。身为工程师的他还兼营了一个从事房屋租赁的家庭公司。“其实就是擦地板、清烤箱和割草什么的。”梅琳达回忆道。全家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忙碌中度过。梅琳达16岁那年的一天,父亲带回家一台苹果III型电脑,她一下被迷住了。“那时候,我们帮着父亲管理业务和记账,”她说,“看着资金进进出出。”
生活一向爱开玩笑。不过,发生在梅琳达身上的故事最令人称奇。她嫁给了美国最富有的人,住在华盛顿湖畔一座巨大的高科技豪宅里,还为慈善事业投入了几十亿美元。14年前,她和比尔•盖茨结婚,其实也是和自己做了个交易。一方面,她成了全球第一慈善基金的两名合伙人之一。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拥有376亿美元资产。沃伦•巴菲特贡献了其中的34亿。此外,巴菲特还答应未来几年内捐赠共900万股伯克希尔-哈撒韦(Berkshire Hathaway) B股。按当前市值,这批股票总值达410亿美元。如果伯克希尔股价继续上涨,盖茨夫妇也将不断地个人财产转移到基金会,他们二人可能会在有生之年捐出1,000多亿美元。目前为止,基金会为慈善事业共支出144亿美元,哪怕算上通货膨胀,也超过了1913年成立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
另一方面,一直以来,梅琳达牺牲了自己的隐私、安全和普通人的简单生活。她的丈夫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微软反垄断案审判期间,被视为最大的商界恶棍。嫁给比尔•盖茨,是否就意味着将在他的影响下逐渐失去自我,最终成为一个附属品呢?
为了不成为一个附属品,梅琳达些许矫枉过正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下面是她典型的一天:上个秋季的某天,她先在孩子们的学校花费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分别是5岁、11岁的和8岁);之后又招待了10多位客人,其中包括前来西雅图参加基金会疟疾论坛会的4位非洲国家卫生部部长。10点客人们都离开后,疲惫的她又开始担心第二天早上的演讲。比尔对她说:“不如早点休息好了,你已经知道很多疟疾的事了。”尽管对聚光灯心存恐惧,第二天她仍然站在3,000多名科学家、医生和卫生官员面前,公布了一项大胆的计划,旨在根除疟疾——一种肆虐好几世纪,每年导致100多万例死亡的疾病。稍后,她和比尔一起回答了听众的提问。尽管在座的听众大都获得盖茨夫妇数亿美元的捐款,他们并不清楚台上发言女性的身份,不由议论纷纷。
现年43岁的梅琳达•盖茨已经准备好把完整的自己展现在众人面前。“我经常想,等小女儿也上学以后就走到台前来。”她对《财富》记者说道。这是他平生接受的第一次专访。她承认,自己更愿意永远远离公众。不过,大女儿令她重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非常希望她不管从事什么职业,都能有发言权。”她说。“我要为她做出榜样。”她目前花在基金会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达到了每周30小时。“回顾历史上出色的女人们,我发现她们都是以自己的方式走到公众面前的。”
梅琳达决定走出幕后的另一个原因,是丈夫比尔也正有同样的打算。比梅琳达年长九岁的比尔计划自7月份起,每周至少拨出40小时用在慈善事业上,只留15小时左右给公司工作。盖茨夫妇的朋友们说,要不是为了梅琳达,他才不会做如此调整。他们还说,是梅琳达让比尔变得更开放、富于耐心和同情心。“胡说!”比尔吼道。大概意识到自己太没礼貌了,他改口:“没这回事!”但脸上却露出了笑容,因为朋友们说的都没错。有一件事,他倒是欣然承认:他能轻松地适应慈善家这个新角色,还要多亏梅琳达的帮助。谈及慈善事业,他说:“要是我一个人做就没意思了,也做不了这么多。”
严格说来,盖茨夫妇的婚姻并非门当户对。学历方面,梅琳达高于比尔。她持有杜克大学计算机和经济学双学位,以及MBA学位;相比之下,比尔是哈佛大学最著名的辍学生,尽管去年6月他获得了哈佛的荣誉学位。体育方面,梅琳达也胜过比尔。她每周和朋友来一次时速达7英里的长跑,外加5次左右的其他锻炼。她曾跑完西雅图马拉松赛全程,还只凭绳索和冰爪登上了4,392米高的雷尼尔山山顶。比尔呢?梅琳达说:“去年他终于开始跑步了。”比尔并非一无是处,他打网球很是积极,高尔夫水平也不错,有时还会和梅琳达一起打。除了这些,要想不落后于积极锻炼的梅琳达,他能做的也就是每周三次趁着晚上看DVD的时间在跑步机上跑步。
比尔还承认,梅琳达比他更了解别人的心理。他通过梅琳达了解了不少微软内部的人事问题。2000年,和比尔共事了28年的史蒂夫•鲍尔默(Steve Ballmer)接任他成为微软新CEO,是梅琳达的帮助缓解了交接中可能出现的棘手问题。“梅琳达常和我一起讨论问题。”比尔说。“如果能有位红颜知己这么对你说:‘你觉得某某人爬到你头上了?也许他其实没这个意思,是你自己弄错了。’那你真是获益匪浅。”1991年就与盖茨夫妇相识的好友沃伦•巴菲特说,“比尔确实很需要她。”
梅琳达的影响在涉及投资慈善事业时更为显著。很早以前,她和比尔就决定只集中资助几个领域,具体哪个领域取决于以下两点:哪些问题影响人数最多?哪些问题一直被忽略?很多慈善家也是这么做的,不过热衷猜谜的盖茨夫妇执行起来分外精确和严格。梅琳达说,“我们把那些最主要的不公正问题一个一个地列出来,然后把钱投入到可能见效最大的地方。”因此,艾滋病、疟疾和肺结核等最致命的疾病,以及美国国内无法维持下去的公立高中,先后获得基金会数十亿美元的资助,而美国癌症协会(American Cancer Society)不在他们的捐助之列。很自然,盖茨对大概等上几十年才会有结果的疫苗及其他科学研究不感兴趣,梅琳达也更愿意致力于能立即减轻痛苦的办法。“不能指望有疫苗孩子们就安全了。”她说。“比如我来到印度某个村庄里,以为救了那些孩子,但同时牛的排泄物正顺着水流污染整个村子。有很多其他事情等着我们去做。”
比如,资助生产隔开携带疟疾的蚊虫的杀虫剂处理蚊帐;供应防止艾滋病传播的杀菌剂;提供小额贷款和保险,扶持基础最薄弱的小企业和农场成长。两年前梅琳达的肯尼亚之旅,使他们萌生了在非洲进行一场绿色革命的想法,这与1940年期间增加拉美和亚洲农作物收益的那个项目类似。2006年,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建立了1,500万的合作项目。“梅琳达擅长整体思考,”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朱迪丝•罗丁(Judith Rodin)说,“她能和比尔一起深入研究问题。尽管他们迫切地想要做出成绩,但从来不异想天开。他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效果。”
梅琳达的全盘思考能力,加上比尔的智慧,就是效果的保证。盖茨夫妇的朋友、摇滚歌星波诺(Bono)形容他们是“共生关系”。波诺也是个人道主义者,曾在One antipoverty campaign(全球消除贫困与对抗艾滋病的组织)活动中得到盖茨的资助。提到比尔暴躁的情绪,波诺说:“我有时叫他‘杀死比尔’(Kill Bill,好莱坞电影——译注)。这类人——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很容易被激怒,看到大量的生命损失,我们会感到愤怒。我们需要一个不那么冲动的人帮我们保持理智,而梅琳达就是那个人。”巴菲特也认为,是梅琳达让比尔成了更出色的决策者。“很显然,他不是一般的聪明。”巴菲特说。“但是梅琳达更有大局观。”如果没有梅琳达参与,巴菲特会把财产捐给盖茨基金会吗?“这个问题问得好。”他答道。“难说。”
每天一个目标
如果你成功了,那是因为某时、某地、某人给了你生命或指向正确方向的思想。还要记住,这是你欠生活的。要一直像你得到帮助那样,帮助那些没有你这么幸运的人。
——梅琳达•盖茨的告别演说,乌尔苏拉学院(Ursuline Academy),1982年
威廉•H•盖茨三世的父母,比尔(Bill)和玛丽(Mary),都是西雅图抛头露面的领袖人物。而梅琳达•弗兰奇则不同,她的字典里没有特权和财富这两个词。梅琳达有一个比自己大14个月的姐姐和两个弟弟。她的父亲任职于LTV的空间栏目;母亲则是一个家庭主妇,一直后悔自己没有上大学。梅琳达说,“我父母对我们说:‘不管你们考上哪个大学,我们都会替你们付学费的。’”
那台苹果III型其实是家里购置的第二台电脑。梅琳达14岁那年,父亲为她买了台苹果II——市面上第一台消费者电脑。“我想办法它弄到我的卧室里,这样就方便玩游戏了。”她说。她学会了用BASIC编程,还在暑假时教给其他孩子。
生活是一场考试,而梅琳达认为自己必须拿到A。梅琳达在乌尔苏拉学院(达拉斯的一所天主教女校)时的数学和计算机老师苏珊•鲍尔(Susan Bauer)回忆道:“她每天都有一个目标。”提到这句话,梅琳达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其实就是跑一英里、学一个新单词这类目标。”高中一年级时,她翻看了往届毕业生的大学择校情况。她发现,乌尔苏拉只有最优秀的两名学生能进入精英大学。“我意识到进一个好大学的唯一途径是成为能在毕业典礼上致词的学生代表。那就是我的目标。”她解释道。当时,她想进入的是美国圣母大学(Notre Dame)。
想必我们高中时代都遇到过这样的女生吧:名列前茅的学生,复习小组组长,医院里剥糖的志愿者,铁路那头小学校里的助教。梅琳达就是这种女生。乌尔苏拉的校训是“Serviam”(拉丁文“我愿意服务”的意思),志愿服务是学校要求之一。鲍尔强调,梅琳达的野心“从不会让人觉得她无礼。她总是惹人喜爱而有魅力,以自己的说服力赢得人心。”
她得到了在毕业典礼上致词的机会,也被圣母大学录取了,不过她并没有接受。她回忆道,和父亲一起参观学校时,工作人员告诉他们“计算机只是一时的流行而已”,学校正在缩减计算机系。“我一下被打懵了。”梅琳达说。当时正在扩大计算机系的杜克大学得到了梅琳达。她在五年内完成了文学学士和MBA学位。稍后,她在IBM暑期实习时遇到的一位招聘人员把她引向了微软。“我告诉那位招聘者,我还有一个微软——一家新成立的公司——的面试机会。她对我说:‘如果你被他们录用了,那就去吧。他们有相当大的进步空间。’”梅琳达回忆道。
和老板约会
1987年,22岁的梅琳达来到西雅图,负责前一版Word软件的市场工作。那时的她对微软将给自己带来的一切还一无所知。“那儿有很多形形色色有特点的人,都很聪明。他们在一点点地改变世界。”她说。身为最年轻的新员工和10名MBA中唯一的女性,她一点也不担心,影响到她的是微软的企业文化。她回忆道:“公司里的人都很尖刻。”微软从上到下都是如此,盖茨和鲍尔默从来不放过那些经理,带头对着他们长篇大论。那个时候,梅琳达开始考虑离开微软。
然而,四个月后转机出现了。那是她第一次到纽约出差,参加一次个人电脑博览会。聚餐时,她在CEO身边坐下:“他确实比我想象的要风趣。”那么,她又是哪里吸引了比尔呢?“大概是外表吧。”比尔说。
那年秋天的某个周六下午(“每个人周六都上班,”她说),梅琳达和比尔在公司停车场里相遇了。“我们聊了会天,然后他说,‘从周五晚上开始你能和我约会两个礼拜吗?’我说:‘周五之后的两个礼拜?我觉得这样太不自然。快到那天的时候再打电话给我吧。’”当天晚些时候,比尔打电话给梅琳达,飞快地报出一长串他要参加的会议和其他活动。“于是我答应当晚见他。”她说。
这个骨瘦如柴的聪明人刚刚因1986年的微软IPO而成为亿万富翁。然而,亿万美元也买不来爱情。当被问及梅琳达是否装得难以接近时,比尔的回答是:“她就是很难接近!”梅琳达与母亲都觉得和公司CEO约会不太合适。不过据比尔说:“我们发现互相被对方深深吸引着。”梅琳达绝对不会让他们的关系影响到工作。“我不想我们的事情被曝光。我也绝对不会找他帮忙工作上的事。”她解释道。“结果到最后,比尔抱怨说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尽管和CEO谈着恋爱,梅琳达•弗兰奇工作起来可是毫不含糊。在微软的九年里,她一路晋升到信息产品总管(负责Expedia、Encarta和Cinemania),手下有300名员工。她的纪录并非完美无缺。还记得专为怕用电脑的人设计的Microsoft Bob吧,那就是她的杰作。(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点太可爱了”。)不过,就算遇到问题项目,她也能带领团队一起克服困难。梅琳达在微软的前老板、现盖茨基金会CEO帕蒂•斯通西佛(Patty Stonesifer)说,“如果她还留在微软,现在肯定是高管层一员了。”
梅琳达对于嫁给比尔还是有所顾虑。“比尔有钱。”她说。“对我来说,这就像,嗯,他有钱,没什么大不了的。”她明白成功对比尔而言意味着什么——没有隐私,没有过普通生活的权利。比尔征服世界的资本主义天性能否与家庭生活共存呢?他们都考虑过这一点。梅琳达问自己:“嫁给这样一个工作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
奥马哈的一位朋友调剂了他们的关系。1993年复活节的那个周日,比尔和梅琳达来到棕榈泉度假住住宅和父母小聚。不久,比尔提出该回西雅图工作了,于是他们回到私人飞机上。飞行员宣布了路线,比尔拉下遮阳板,拿出一副七巧板转移梅琳达的注意力。(“比尔很擅长复杂的七巧板,但梅琳达水平好得难以置信。”巴菲特说。)飞机降落了,舱门打开,“沃伦拿着喇叭站在那儿。”梅琳达回忆道。(这里不是西雅图,梅琳达。这里还是奥马哈!)巴菲特开车带他们前往伯克希尔-哈撒韦旗下的一家珠宝中心,一路还不停地开着玩笑:“比尔,告诉你一套衡量爱情的标准吧。苏西的戒指的价值是我净资产的6%。我不知道你有多爱梅琳达,但在奥马哈,6%是最起码的。”比尔那时候身家73亿。梅琳达逛街的时候比尔却在询问商场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我想要个祖母绿,不过比尔认为钻石更合适。”梅琳达回忆道。她选了个没有巴菲特定的价钱那么高的钻石。
大约那时起,比尔和梅琳达就开始讨论如何把他们的钱捐出去。尽管不少人责难比尔太吝啬,他们还是想等比尔60岁以后再做打算。“律师和会计师们都曾建议他成立一个基金会。”比尔的父亲回忆道。“但他拒绝了,说没必要再另建一个机构。”1993年12月梅琳达的告别单身派对之后,他们的想法改变了。派对上,比尔的母亲玛丽•盖茨朗读了一封写给梅琳达的信,大意为“多得者也应多给与”。次年6月,一直在与乳腺癌作斗争的玛丽•盖茨辞世,她生前的教诲促成了盖茨名下第一个慈善团体——威廉•H•盖茨三世基金会(William H. Gates III Foundation)——的成立。比尔的父亲为此用光了地下室里的纸盒。
梅琳达回忆道,起初我们打算给教室配备笔记本电脑,不过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软件大亨给自己创造市场的行为。当时,她正在西雅图的几所学校担任义工,她意识到学校的问题远不止硬件。于是,她和比尔决定广泛推行中学教育改革:“中学的问题看来最棘手,没人愿意碰。”
婚后不久,他们就遇到了全球健康问题。梅琳达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头版上读到一则报道,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儿童死于美国人都没听过的疾病,比如每年导致50多万儿童死亡的轮状病毒,还有在美国几乎已经见不到的疟疾和肺结核。“我想,这太可怕了。”梅琳达说。之后,她留了张纸条给比尔。(“这是我们工作的方式。”她解释道。“我们一直互相在办公桌上留纸条。”)比尔从那篇文章里了解到,1993年的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计算了这些疾病造成的损失。他找到这份344页的报告,读了几遍后,也给梅琳达写了张纸条:“我不会做这种事情。我有不同的学习方法,我从试验中学习。”
巴菲特的礼物
“没错,我们就是那种边在海边散步边讨论化肥还很乐在其中的夫妇。”比尔自豪地说。我们坐在微软的主席办公室里聊着,比尔在摇椅里前后摇晃——这是梅琳达没有纠正的一个旧习惯。“梅琳达的思维更科学,而且她读的书比你认识的人中的99%都要多。”他说。盖茨夫妇通常在书房里审核资助,或是一边散步一边详细商讨(基金会每年收到的大约6,000份申请里,他们只亲自评估多于4,000万的那些申请)。讨论时,他们一般不把资料摆在面前。正如梅琳达所说,“你最好把信息都存在脑子里,这是锻炼记忆力的好机会。”
去年9月,梅琳达在纽约举行救助儿童(Save the Children)的晚宴,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捐赠了当晚所用礼品。提及两年前和盖茨夫妇的南非之行时,他说,那时他和比尔•盖茨都“自认为非常聪明,表现得无所不知,问题也以为都问到了点子上。而梅琳达只是耐心地坐着,等我们都不说了,她才插空提了几个问题:‘教育方面你们有什么打算呢?预防方面呢?有多少人在使用避孕套?’” 两个比尔一听都蔫了。“女人在某些关键时刻要比男人理智 。”克林顿说。
梅琳达把脏兮兮的艾滋病患儿递到丈夫怀里,比尔表现出了明显的同情,只是没有梅琳达那么自然。梅琳达的好朋友、已退休的惠普(Hewlett-Packard)和微软高管、现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会一员的夏洛特•盖蒙(Charlotte Guyman)回忆起2004年的加尔各答之旅。一天,梅琳达需要参加基金会的会议,盖蒙和另外几个同行的人在特瑞沙修女临终关怀之家(Mother Teresa's Home for the Dying)待了半天。他们在那里遇到一个深受艾滋病和肺结核之苦的“只剩一副骨架”的年轻女人,他们都被她僵尸般的凝视震住了。第二天,梅琳达也来了。“梅琳达走了进来,顿了顿,然后径直走到那个女人面前。”盖蒙回忆说。“她拉过把椅子,把那个女人的手放到自己的手里。那个女人根本不看梅琳达。接着梅琳达说道:‘你有艾滋病。这不是你的错。’她又说了一遍:‘这不是你的错。’泪水顺着那个女人的脸哗地流了下来,她看向梅琳达。”盖蒙忘不了当时她们之间的情绪交流:“梅琳达就那么坐在她身旁,时间仿佛静止了。”
如此近距离地感受痛苦,使盖茨夫妇决定把更多的钱花在他们称为干预的方面:床帐、避孕套、杀菌剂(无色、无味的妇女外用凝胶)。这些可以在救命稻草——疫苗到达前,帮助人们避开疾病和死亡。看到艾滋病在发展中国家妇女间的肆虐,虽然自己信教,梅琳达并不为资助推广避孕套等受到保守派罗马天主教徒质疑的项目而愧疚。“避孕套能救命。”她说。
尽管盖茨基金会实力雄厚,梅琳达仍坚持他们需要合作伙伴。她说,“NIH(全国卫生研究所)的预算是290亿,加州州政府一年的投入是600亿。比较之下,我们仍然囊中羞涩。要是我们也那么大手笔,基金会就办不下去了。”因此,盖茨基金会和其他几家慈善机构[迈克尔和苏珊•戴尔基金会( Michael and Susan Dell)、休伊特(Hewlett)基金会]及几家公司[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宝洁(Procter & Gamble)等]就不同项目结盟合作。最成功的联合体当属由盖茨基金拨款15亿美元帮助建立的Alliance,其全称是“全球免疫预防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Vaccines and Immunization,GAVI)。在欧盟及17个捐助国的共同努力下,GAVI为70个最贫困国家的1.38亿儿童提供了破伤风、乙肝及黄热病疫苗。多亏了GAVI,发展中国家的免疫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多万幼儿远离了死亡的威胁。
美国国内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只有70%的九年级学生能按时高中毕业,教育改制的路途异常艰难。梅琳达承认,她和盖茨以前想得太天真了:“我以为只要我们开办了足够多的学校,人们就会说,‘不如我们也照样建一所学校。’事实恰恰相反,你可以立马建上1,000所学校,但在现存教育体系中水平根本得不到保证。”在丹佛到盖茨家的后院西雅图,盖茨夫妇对教改的投入和回报并不成正比,学校既没能与社区有机地融合,也没能培养出学生的领导能力。目前,盖茨尽可能地联合学校领导和市长、州长等官员的力量,一起对1,800所高中进行整改。“事情总是时好时坏。”梅琳达说。
然而,纽约向人们展示了盖茨的实力。43所盖茨基金会资助新建的小型高中毕业率由先前的35%上升至73%。盖茨夫妇在这一领域的合伙人恰好是乔尔•克莱恩(Joel Klein)——十年前司法部反微软垄断案最高负责人,现在掌管着纽约市的教育。克莱恩充分意识到这次合作的讽刺意味,他称他们之间关系的进步是“给比尔脸上贴金”。比尔那方面则表示,自己不介意把钱交给之前的对手,梅琳达则对那段时间产生的矛盾不做评论。她说:“我不想公开这部分内容。”但显然,她帮助丈夫接受了需要与克莱恩共事的事实。“比尔这点很好,”她说,“他知道要向前看。”巴菲特评论道:“当比尔拿出5,000万美元给乔尔•克莱恩管理下的学校时,我就知道他确实是个识时务的人。”
有了巴菲特这个重量级的合作伙伴,盖茨夫妇掌握了更多的资金去完成他们的计划。巴菲特本打算一辈子死守着自己的财产,2004年妻子苏西去世时他改变了主意。2006年春,他在多次提示之后,向比尔坦承了自己的想法。比尔回家后讲给梅琳达听,他们一起走了很久,都哭了。梅琳达回忆道:“我们彼此对对方说:‘天哪!你知道替别人捐赠他们的财产将会是多大的担子吗?’”
巴菲特托盖茨夫妇在第二年内发放出所有他的年度捐款。他还提了一条建议:“专注于目标。”他认为,把捐款交给盖茨夫妇打理,是“完美的解决方法”,这既因为他们是慈善业的行家,也因为他在比尔身上看到了自己,而在梅琳达身上看见了已逝的前妻。“以前比尔是个奇怪的家伙,容易走极端,但自从和梅琳达在一起,就好多了。”他说。“同样、,苏西也令我不再那么极端。”比尔怀着喜悦和感动的心情发放了巴菲特的十亿捐款。他的话也证实了巴菲特所说的:“沃伦知道拥有梅琳达对我来说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我们让他回想起和苏西在一起的时光,设想和苏西一起捐款的情景。”
比尔和梅琳达眼下的任务是合理安排两人间的分工。盖茨基金会目前已有员工500名,未来两年内还将翻番,合理分工对管理这样一个大机构而言至关紧要。比尔向来对团体或组织什么的不太上心(倒是鲍尔默比较热衷)。他更倾向于和科学家及研究人员打交道,比如一起探索教学所需的技术,怂恿制药公司研制在发展中国家用不到的疫苗,等等。“不然没人督促他们,”他抱怨道,“那种工作天生适合我。”相比之下,梅琳达更乐意专注于人员和文化问题。有批评指出,只有和盖茨夫妇关系密切的基金会管理人员才握有实权。梅琳达表示,她希望能逐层下放决策权。当被问及关于基金会官僚作风的批评是否属实时,她回答道:“当然,有些是真的。”她继而解释说:“几年前有人称赞我们的评估速度很快。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就算能立即发放资金,却得不到期望的效果。我宁可按部就班慢慢来,也要让效果得到保证。”她还提及有人指责基金会投资给商业兴趣可能与基金会慈善目标相矛盾的公司,比如英国石油公司(BP)和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等,她认为他们必须对此采取措施。为此,去年5月,梅琳达和比尔派出捐款管理人员前往苏丹出售基金会所投资公司的股份。
住宅危机
1994年1月1日,梅琳达和比尔在夏威夷拉奈岛上举行了婚礼。梅琳达最喜欢的歌手威利•尼尔森在婚礼上献声,这当然也是比尔安排的小惊喜了。事后梅琳达说道,她面临了“一个很小的个人危机”,根源是比尔在西雅图郊外华盛顿湖畔建的房子。那栋房子是任何一个单身汉的梦想,可也是新娘的噩梦:约3,715平方米的面积,包括几个车库,一个放蹦床的房间,一个室内游泳池,一个带爆米花机的影院,再加上多到让新婚的梅琳达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在电脑游戏里软件和其他高科技设施之中。“如果我真的要搬进去,”她想起当时在电话里对比尔说的,“那就得像我想要的样子——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家庭生活。”
装修完工前,盖茨夫妇就搬了进去,事后证明这是个错误。“周围的一百多个工人让她觉得‘以后的生活就是这样了’。”比尔说。他曾经让梅琳达“每天说出你喜欢这个房子的一个地方。”梅琳达回忆道。“我会说:‘行,我喜欢那个衣物滑槽。’要么是,‘行,我喜欢这个地方,不过不喜欢这十个地方。’”
住房象征着梅琳达对正常生活的渴望。让孩子们过得越平凡越好,是她的首要目标。于是,她坚持每个周末除保安外所有雇工都要离开,遇到和比尔出去锻炼、吃饭或看电影的时候,才会在当天晚些时候安排一位临时保姆。每周三晚上,是全家的游泳时间;每周五晚上,是看电影时间。波诺曾在盖茨家住过几次,他说:“那个家有它自己沉静的一面,有那么点‘禅’的味道。这都是梅琳达的功劳。”他们有时在光线充足的临湖厨房里小聚。波诺说:“和他们一起瞎混,很有意思。比尔喜欢黑色幽默,梅琳达和他经常一捧一逗。”
梅琳达很赞同波诺的描述。但她是否喜欢这栋房子呢?“现在我喜欢这里。”她笑着说。“要是我来设计的话,不会建成这样,但我挺喜欢它现在的样子。”
盖茨的子女已到了想了解父母所作所为的年纪。2006年,梅琳达和比尔带着两个大孩子前往南非,参观了开普敦的贫民窟和一所孤儿院。然而,他们发现很难向孩子们解释慈善工作的价值。几年前,他们给孩子们放了一段关于小儿麻痹症的纪录片,看后孩子们问起电影里的一个跛脚男孩:“你们帮助那个孩子了吗?你们知道他的名字吗?那又为什么不知道呢?”这样的问题一个接一个。“我们不认识那个孩子。”梅琳达这样告诉孩子们。“但是,我们努力帮助很多和他一样的孩子。”比尔的解释则是:“我从事的是批发,不是零售!”
比尔说他们的孩子“知道他们的钱比谁都多”。当然,孩子们也问过父母是否会像十亿十亿地捐助穷人那样慷慨地对待他们。“我们告诉他们:‘不用担心,你们手头会很宽裕。’”比尔说。尽管他和梅琳达已经计划好有生之年捐出95%的资产,但还没想好将剩下资产里的多少留给孩子们。梅琳达说,他们会遵循沃伦•巴菲特的原则:“有钱人应给子女留下足够创业的钱,但不能多到让他们不用做事。”
“我有什么重大缺点?”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采访期间,梅琳达大笑着说。她承认,有时自己想要更简单的生活。“不过这取决于你什么时候问我。大多数时候我会说不想,但要是昨天你问我想不想过更简单的生活,我会回答:想。”昨天是指那次疟疾论坛的前一晚,她怀着不安的心情上床睡觉。今天早上她站在台上,仔细观察着台下那些著名医生和卫生专家,给自己打气:“我告诉自己,‘我认识那个人……我知道些他的研究……她的研究我也知道……’”“我对自己说:‘可我了解得还不够多。’”尽管紧张,她还是完成了自己今天的目标:呼吁根除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行病。明天她将面临另一个目标,也许更具挑战性。
译者:项婉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