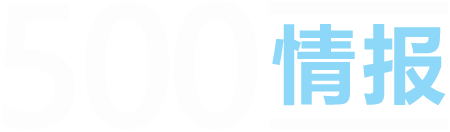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波本酒大繁荣
似乎为了彰显波本酒的全球化身份,今年1月,日本的烈性酒和饮料巨头三得利(Suntory)突然宣布160亿美元的出价,要收购占边公司(Beam Inc.)。占边公司拥有吉姆·比姆家族的威士忌品牌,以及拉弗格(Laphroaig)单麦芽威士忌、索查(Sauza)龙舌兰酒和拿破仑(Courvoisier)干邑白兰地。
杰克丹尼(Jack Daniel's)和活福珍藏(Woodford Reserve)威士忌的生产商布朗-福曼公司(Brown-Forman)总经理蒂姆·德隆(Tim DeLong)说:“现在大概是自禁酒时期以来进入波本酒行业的最佳时机。”在过去两年,整个行业已经投入3亿美元,用来扩大产能。开车经过巴兹敦(Bardstown)或是劳伦斯格堡(Lawrenceburg)等肯塔基州威士忌圣地周边的山区,你会看到新建的五层催陈酒库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建造仓库的不只有大公司。过去5年里,新涌现了数百家新的手工酿酒厂。位于纳什维尔(Nashville)的海盗船工匠酿酒公司(Corsair Artisan Distillery)的联合创始人达雷克·贝尔(Darek Bell)说:“我们每年的产量都不够。”
但是,波本威士忌的突然兴起提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尽管某些趋势正在变成新的常态,但另一些趋势仍然遵循重力定律,它们的衰落和崛起一样快。毕竟,《广告狂人》不会一直在电视上播下去。威士忌行业以前遇到过泡沫,当需求的飙升推高了产量,消费者的口味却突然改变,令需求一落千丈。好运完了,知名品牌从此消失,整个行业一片凄凉。这一次,各酒业能够避免重蹈覆辙吗?
要参观波本酒上次繁荣的遗迹,请由肯塔基州首府法兰克福(Frankfort)向南,沿着麦克拉肯公路(McCracken Pike)行进。绕过一个弯,在一排铁链网的后面,就坐落着一座莱茵城堡的遗址,还有它的日益颓败的城垛和中世纪塔楼。这里是老泰勒酿酒公司(Old Taylor),由肯塔基州的传奇酿酒师和政治家E·H·泰勒(E.H. Taylor)在19世纪末所建,曾经是最著名的美国威士忌品牌之一。
老泰勒公司活过了禁酒时期[后来被占边公司的前身国民酿酒师公司(National Distillers)于1935年收购];它还活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酒类生产完全停止,酿酒公司为军队制作工业级酒精。事实上,老泰勒公司等酒厂在战后一度繁荣,威士忌和汽水在战后一度成为全国性饮料。历史学家迈克尔·R·维奇(Michael R. Veach)在他的著作《肯塔基波本威士忌》(Kentucky Bourbon Whiskey)里写道:“20世纪50年代是肯塔基州波本酒行业的黄金时代。人们毫无节制地酿造,产量超出了销售预期。”
但问题就在于此。与大多数烈性酒不同(在这一点上或许也与大多数消费品不同),威士忌的生产周期要按年而不是日或周来计算。不管酒厂碾磨谷物或是让原料发酵的效率有多高,一瓶4年的波本酒也必须在木桶里存放至少4年。这意味着酒厂要根据对较长未来的需求预期来确定量产水平。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是波本威士忌的狂欢,那么70年代和80年代就是它的宿醉期:工作岗位消失了,利润暴跌,大酒厂不是关门就是被卖掉,包括老泰勒公司以及由被人称为“老爷子”(Pappy)的朱利安·范·温克(Julian Van Winkle)所创办的斯第泽尔-维勒公司(Stitzel-Weller)。(老泰勒在1972年破产,斯第泽尔-维勒公司坚持到了1991年。)
但各酒企并不愿意接受小众市场地位,它们放下了身段,经常将酒精度数更高、年头久远的波本酒与品质一般的烈性酒混合,创造出一种较为轻淡、柔和的威士忌,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用于调配鸡尾酒。结果造成了恶性循环:聚焦于低端市场品牌强化了波本酒缺少魅力的形象,让年轻人与之渐行渐远。肯塔基酿酒者协会(Kentucky Distillers Association)的主席埃里克·格列高里(Eric Gregory)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波本酒被认为是父辈的饮料,甚至可能更糟,被认为是你爷爷辈的饮料。”
天堂山酿酒公司(Heaven Hill Distilleries Inc.)的总裁马科斯·沙皮拉(Max Shapira)说:“分析师基本把我们归入行将就木的公司之列。”他的公司生产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与推特公司(Twitter)的联合创始人无关]等品牌的波本酒。业内很多人也同样悲观:1999年,各酒厂只生产了45万桶,比波本酒的鼎盛时期减少了将近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