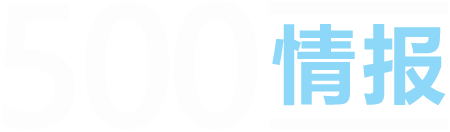走访杰米·戴蒙
摩根大通银行(J.P. Morgan Chase)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这几年日子不好过——从华尔街崩溃到金融业的房贷抵押信用危机。尽管他的公司比其他金融服务机构更为顺利地渡过了这次难关,但对这位世界第二大银行的负责人来说形势已经完全变了。《最后一个站立的人:杰米·戴蒙与摩根大通的崛起》(Last Man Standing: The Ascent of Jamie Dimon and J.P. Morgan Chase)一书作者杜夫·麦克唐纳(Duff McDonald)在2010年9月24日与戴蒙一起坐谈其世界观。(采访结束后,《财富》记者请戴蒙谈谈对摩根大通暂停止赎的看法。他还提到,一位公司发言人曾说:“我们认为有关房贷的文件里的信息是正确的,若是我们一旦发现任何错误都会纠正过来。”)以下是这次采访的摘要:

在经济二次探底的情况下,你们的优势在哪里?2010年早些时候,您基本否定了再次探底的可能,但从那以后经济并没有回升的迹象。
我不认为会有二次探底,但实际结果如何,谁也无法预测。美国经济也许比人们想象的更加强劲。我乐观的根源来自美国固有的实力——其中有许多有赖于商业——丝毫未损。我们努力工作,我们积极创新,我们有很快的适应能力。美国一旦恢复了它的魔力,谁都会感到吃惊的。
最大的威胁是什么?
你读过卡门·雷恩哈特(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戈夫(Kenneth Rogoff)写的《这一回不一样:八个世纪的金融界蠢事》(This Time It'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吗?这是本学术性很强的书,但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历史事实是,许多政策的实施结果有可能事与愿违。我们在央行政策、贸易政策甚至汇率政策上都见过这类情况。最大的威胁也许恰恰是我们自己。
说到政策,哈佛大学法律教授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在对华尔街肥猫们的指控中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您。截至去年9月,她仍在主管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您与她共事感到很兴奋吗?
她在任命公布那天打电话给我。我当时在俄罗斯,否则我会先给她去电话的。我的工作就是与监管当局协作,做好这项工作,并且永远竭诚为消费者服务。我希望她能有所成就。至于她说过关于我的话,我个人并不当回事儿。
她的话里有一段是对您的回应,因为您说过金融危机每10年左右就会来一次,生活本来就是这样。而且她并不是唯一做出回应的。人们对您的话感到愤怒,您不意外吗?
我觉得我能解释清楚。我当时说这话的意思是,你需要做好应对坏天气的准备。我不是认为它是件好事,只是说我们不应该在它出现时如此大惊小怪。有人把此话理解成了“我们对此无可奈何,不必抱怨,只需应对”,
我完全赞同我们不必对它逆来顺受的说法。许多这类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我猜想,再往后一千年,人们回头看我们如何应对危机时,很像是我们看早年医生给病人放血一样。处理错综复杂的经济难题和危机的工具会变得比现在高级多了。
您最近说过,我们的监管体制得到了加强,但没有简化。要是您来做,会有哪些不同?
我们一向承认,许多事情应该解决。比如,要有系统的监管,把衍生工具归到清算中心去,以及提高资本与流动性标准等。我认为他们做了许多此类事情。但是,你看一看监管体制就会发现,我们的监管部门过多,它们的职责之间的重叠也过多。要是我来处理,我会建立一个精悍但又更加强大有效的“银行监管部门”,消除其中一部分重叠。我还会让它们的权限更加清晰。
您还说过,新的金融监管体制“没什么大不了的”。您是否轻易就摆脱它了?
我在说这话之前也说过,立法也许会产生我们无法预见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至于我们能预见到的后果,我说过我们能够应对。也许我说它“没什么大不了的”是措辞不当。我的真实意思是,如果你拥有这家公司——我当时是在对一屋子投资人讲话——我们就仍然能为客户和股东做好服务。我当时只是在说摩根大通。我觉得这项立法的后果也许对某些竞争者更有利,对某些竞争者则更不利。比如,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上,外国银行占的便宜可能会大得多。
在您所谓的“示好”一事上出了许多岔子,到头来和奥巴马掰了。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我俩从来没有好过,也谈不上掰。我还在和政府的人交往。他们做的事我不全赞同,也不全反对。他也许有许多密友,但不包括我。
您曾经提到过,等您离开摩根大通后会以某种方式进入政坛。您现在是如何想这件事的?
我从未特意说过要从政。我说的是为国效力。我一直后悔没在军队服役过。但我现在没有这个意思,我也没有指任何具体的工作。至于政坛,机会也许已经早就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了。但我是个强者——我能处理好的。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您为了卖掉在芝加哥的住房不惜降价好几百万美元。
我还没卖掉呢——我还在谈价钱。如果这事让别人高兴,那就太遗憾了。但是如果有人在房地产上亏了钱后看到我也亏钱会觉得好受一点的话,我能谅解。倒霉蛋需要有个伴。
根据媒体报道,摩根大通打算放弃在伦敦金融区金丝雀码头建新总部大楼的计划。这真的是因为您让英国对大银行的税收政策给惹恼了?
我们还在探讨新总部的选址问题。我是觉得税收问题很严重,不公平,但这和建总部毫无关系。我们会永久留在英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这一个篮子,里面装着许多鸡蛋;而且,我们也许得稍微多考虑一点地理位置的多元化。我无法告诉你结果会如何,因为我们正在磋商。但我们会做成最合算的生意。
对金融服务改革,人们似乎仍然在苦苦思考哪类风险承担机构可以从事这一行。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和许多人都认为,像摩根大通这样的储蓄银行根本不该做投机业务,而是应该继续做信贷业务。这两者如何平衡才对?
人们对这场危机的认识是,某些机构若冒了太多的风险,遇到经济衰退便会不堪一击,身受其害的就不仅是它们的股东了。它们会破坏整个体系,进而殃及纳税人。这就是我们支持设立解决机制的原因,而且我们总是留有足够的资本。
但是,金融服务公司就得承担风险。你若是不承认人们有时会犯错误,就干不了这一行。我对有关纯自营账户交易的争议并不在意,但对如何定义做市与自营持仓盘之间的区别特别较真儿。我不认为从事贷款业务比别的业务高尚多少。我们向许多人提供资本和本金。不过,我们要冒什么风险,应该靠我们自己的主观判断,只要我们避免过分冒险就行。
这是不是我们陷入当下困境的缘故?有一群所谓的高智商金融首席执行官就是这么干的吧?
有人这样做,也有人不这样做。
译者:王恩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