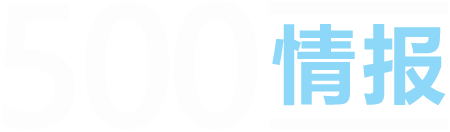陶氏化学的新方向
陶氏公司眼下的战略是什么?
眼下是公司的第三次大转型期。115年前初创时,它是一家无机化学公司,后来变成了一家石化和塑料公司。在过去七、八年里,它转向科研型企业,即采购原料并为其增值。所以,大宗商品的产量减少了。我们正在引进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和材料科学。
你们正在紧跟四大潮流:清洁能源、健康与营养、新兴经济体的消费热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从经营的角度看,是哪个趋势引导你们转向的?
是技术研发——过去5年里,我们向跟随这四大潮流的研发项目投入了90亿美元。我们在研发方面是以创新为中心,这是个重大变化。我们如今能吸引到全美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才,世界各地的人才也来我们公司。我们的用人策略随着我们的宣传策略一起改变,围绕着人的因素和可持续性重塑公司形象,突出以创新为核心,而不是过去那种生产大宗化学品的老牌公司。
还有营销。我们所在的领域不是消费领域,但从消费者心理的角度来看,如果要使他们懂得“内置英特尔”的道理,使他们知道我们拥有能提高洗发香波效力的特殊成分,或是拥有能提高芯片运行速度的特殊材料,或是拥有能使房屋更加隔热,从而成为零能源消耗住宅的特殊材料——如果要使他们了解这一切,我需要开展针对消费者的市场营销。
在这方面,我们也许还要继续努力。在其他方面的改变,我认为我们已经提高了公司的地位:我们不再是陶氏化工,而是陶氏,是一家以可持续业务为主的公司。
你们通过生产太阳能墙面板向消费品市场靠拢。买家也许是工程承包商,但最终拿主意的还是消费者。
这又回到最终用户品牌营销问题上了。你不必和他们直接打交道。只要最终用户了解是你们创造了这种可能性就行。这一点非常重要,原因有很多。我们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接受公众舆论的评判。“可持续”不再是一个选择,它是一个形容词——可持续业务、可持续科学,可持续解决方案。把自己作为一个向普通老百姓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推出来,就能使我们继续深入人心,即便生产的不是消费品,也是在消费领域里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业务,比如太阳能墙面板。
您对在美国制造的主张很热心,您也说过,政府应该对此多加鼓励。但反对意见是,如果企业没有政府刺激便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还算是好企业吗?
我认为,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跑题了,而答案就在这个主张里。我们时代的大部分重大发明都是来自政府出资的国家实验室,如贝尔实验室(Bell Labs)、阿贡实验室(Argonne Labs)、劳伦斯·利弗莫尔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等。其实,是纳税人通过这些实验室创造出了激励因素,并且流向各行各业。把人送上月球,发明互联网,这些全都来自于对国家使命的发人深思的前瞻性回应。
我们当前的国家使命是什么?我们是否只想在世界上当一个服务提供商?还是想成为知识产权提供商,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我们能做得更有效,并且打算向全世界输出?
激励手段不是补贴。我补贴过公司所有的竞争性活动——原料补贴、资金补贴、劳动力补贴。根本就没有公平竞争场地这种东西——我们不要对这个理念太过天真。美国离不开农业和国防,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在制造业,我们考虑过国家的需要吗?依我说,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需要。第一是能源需求,我们面对的是做能源进口国还是做出口国。第二是基础设施。我们必须重新建设国家。这两件事都需要——不是补贴——而是一个政府的整体规划,以鼓励私营部门参与解决。
您认为您关于国家使命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同吗?
我觉得本届政府理解这一点。光是担任先进制造业合作项目的联合主席这一点,我就很高兴了——在三、四年前,我和政府根本没有谈起制造业。如今我们谈了。
我是出生在澳大利亚的美国公民,有幸来到这个伟大的国家,所以我认为,我说这话是有一定目的的。我们现在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有着充满活力的创业意识和创新能力。我们要做的无非是停止相互攻讦,共同开展政府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项目。我认为本届政府一直在努力工作,使先进制造业合作项目开展起来。我很有信心,过了这段政治周期之后,我们会看到有新的举措。
您在同一家公司里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这是当今许多年轻人无法想象的。年轻人是否仍然应该走这条路呢?
人们可能都以为我在这家公司里干了36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实不然。我曾经过一两年就换份工作,而且每隔一两年陶氏公司就再次录用了我。所以,我现在也每隔一两年再次录用公司的年轻雇员,对这一代人也许还不到一年就再次录用了。更年轻的一代不像上一代人那样爱跳槽了。他们有自己的乐子。他们想使自己的环境有所变化。于是,我就得根据他们的兴趣范围加快调整公司文化来吸引他们。我不是在批评谁。这就是个“实际情况”。
所以说,我没有一干就是36年。我曾有过很多机会离开陶氏公司。我进了公司,但我留下来是因为人的缘故。是你周围的人使你感到工作和生活有望变得美好、充满活力。因为你如果不这样想,那你一天天究竟在干些什么?
译者:夏蓓洁